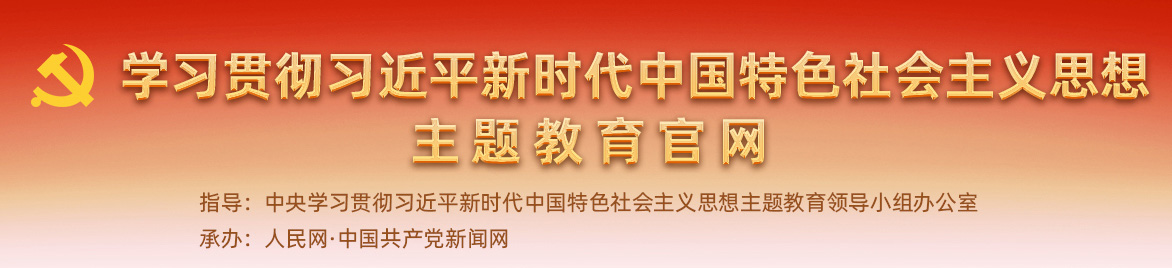你可以是不為任何人開的花
教學樓前的紫荊又開了。每天早八路過時,總能看見整棵樹頂著滿枝的紫,像是誰把晚霞揉碎了撒在枝頭,連石階上都落著星星點點的花瓣。有次蹲下來細看,發現每片花瓣都蜷成溫柔的弧度,像被春風吻過的小扇子——它們開得并不整齊,有的深紫有的淺粉,卻自有一股熱熱鬧鬧的勁頭,讓人想起軍訓時站在太陽底下,汗流進眼睛也不肯亂動的自己。
一、在績點表和涂鴉本之間
記得大二那年,整個宿舍都在卷績點。小楠每天抱著電腦算學分,連選修課都要挑“給分高、作業少”的,她跟風選了門“世界茶文化”,結果發現每周要交兩千字品鑒報告。有天晚上她趴在桌上嘆氣:“其實我根本不喜歡喝茶,只是聽說這門課容易拿4.0。”后來她退了課,跑去蹭隔壁班的素描課。現在她的筆記本上畫滿了宿舍樓的速寫,陽光從紙頁間透過來,比任何成績單都鮮活。
我自己也有過擰巴的時候。大一時加入學生會,每次寫策劃案都要改十幾版,部長總說“再加點熱點元素”。有次熬夜改到凌晨,看著文檔里堆砌的“yyds”、“絕絕子”等網絡熱詞,我突然想起高中時在課本邊緣寫的詩——那些關于云朵和晚自習的句子,早就被塞進了抽屜最深處。后來我退出了部門,把周末還給圖書館頂樓的陽光,當筆尖再次落在紙上時,寫的不再是別人喜歡的格式,而是真正想講的故事。
食堂里常能聽見這樣的對話:“今天去自習室嗎?”“不了,社團要排畢業晚會的劇。”有人為了實習證明放棄喜歡的社團,有人為了一場演出熬幾個通宵。有次在圖書館遇到同專業的學長,他保研名單上的名字旁畫著星號,卻在簡歷最下面寫著“校話劇社三年”。他說:“那些在后臺改臺詞的晚上,比績點更讓我覺得自己在活著。”
二、在考研教室和操場晚風之間
大三的考研教室像無聲的戰場,每個人面前都堆著半人高的資料。隔壁班的阿林卻常坐在操場看星星,他準備跨考天文專業,“雖然數學題難到想撞墻,但一想到能研究星系,就覺得值得”。有次下雨,我看見他蹲在臺階上畫星圖,雨水把紙打濕了一半,他笑著說:“反正宇宙本來就有陰晴圓缺嘛。”
我也曾在考研和就業之間搖擺。秋招時投了十幾份簡歷,每次收到拒信我都懷疑自己是不是選錯了路。直到某天在走廊遇見畢業設計導師,他指著我電腦里的設計稿:“你明明在畫圖時眼睛會發光,為什么要去擠那條不適合的路?”那天傍晚,我坐在畫室里改圖紙,顏料蹭到校服上也沒在意,窗外的紫荊在暮色里輕輕搖晃,突然就想起大一時的自己——那個敢在迎新晚會上唱跑調歌曲,卻笑得最開心的自己。
畢業前最后一次班會,班長讓每個人寫一句話留給未來。有人寫“考上理想的學校”,有人寫“拿到大廠offer”,我盯著紙上的“別弄丟那本涂鴉本”,突然明白:那些被我們小心藏起來的喜歡,那些在取舍時舍不得的倔強,才是成長最真實的印記。就像紫荊不會因為花期短就不開花,我們也不必為了別人的期待,把自己塞進標準的模子里。
每次路過那棵紫荊,我都會想起這四年里無數次的猶豫和堅定。那些被放棄的“正確選項”,那些讓我們咬過嘴唇的決定,原來從不是失去,而是讓生命騰出空間,去盛放真正屬于自己的花。或許我們終會明白,大學教會我們最重要的事,不是做對每一道選擇題,而是在無數個“選A還是選B”的時刻,聽見內心那個小小的聲音——它說,你可以不是別人定義的花,只要你愿意,就能按照自己的節奏,開成喜歡的模樣。
就像此刻在風里搖晃的紫荊,沒有人為它修剪枝椏,沒有人為它標注花期,卻依然在屬于自己的季節里,滿樹滿枝地盛開。這大概就是成長最好的樣子:不被定義,無需迎合,只認真地做自己的花。(編輯/韋欣雨)